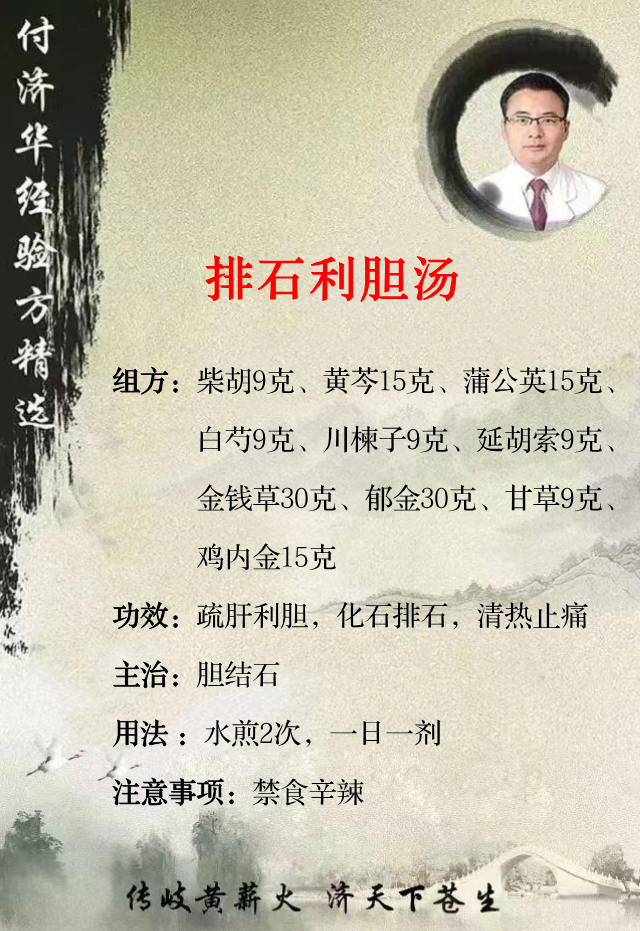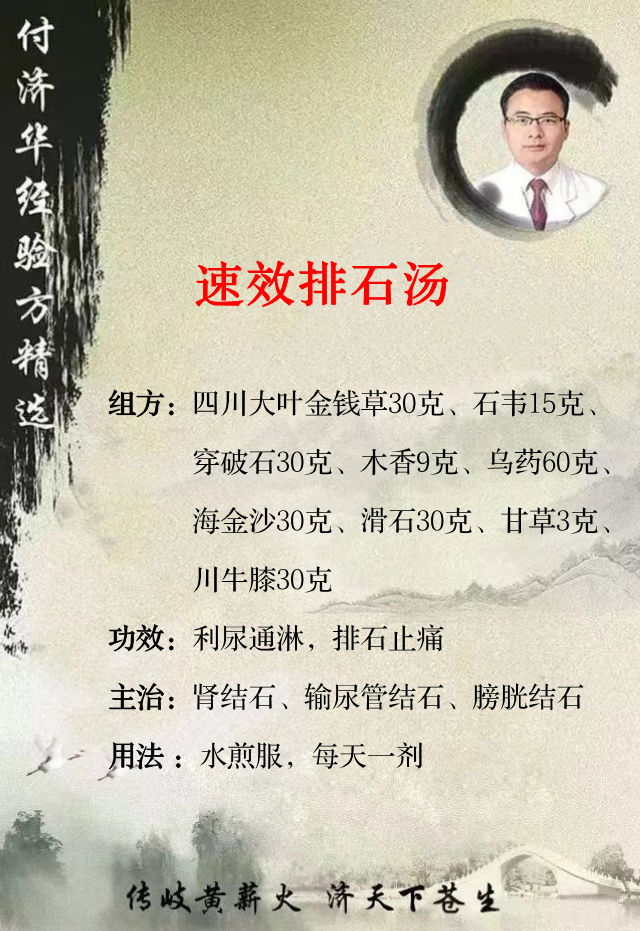腊月十六的清晨,呵出的白气就像是早餐摊的老马在抽烟一样,可是我不抽烟。我搓着手走进药市,一股混杂着甘草、当归和尘土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每年年关前市场特有的味道,少了些喧嚣,多了几分年终盘点的静气。
地骨皮摊前已经围了三四个人,这在腊月里的市场算得上热闹了。摊主老马站在条凳上,用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新价:“过2号筛货,60元整”。粉笔划在黑板上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格外清晰。
“老马你坐地起价啊!”底下有人喊,“昨儿不还五十五吗?”
老马写完最后一个字,拍拍手上的灰,这才转过身来:“张老板,您去整个市场转转,要是能找到比我这儿便宜一块的,今天我请客,东街羊肉馆!”
那位被叫做张老板的中年人没接话,蹲下身从麻袋里抓了一把地骨皮。他捏起几片对着光看,又放在鼻尖闻了闻,这才站起身:“尉氏的货?”
“昨晚上十点到的车。”老马跳下条凳,“就这一车,卖完就得等正月十五以后了。”
张老板沉吟片刻:“五十八。”
“六十。”
“五十九,我全要了。”
老马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张老板,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您知道现在尉氏什么情况吗?加工厂昨儿就放假了,工人全回家过年。这六十,”他拍了拍麻袋,“是年前最后一车的价。”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张老板掏出烟,递给老马一支,自己点上深吸一口:“行,六十。过磅吧。”
这笔买卖做成得干脆利落。等张老板的伙计开始装车时,我才凑过去问:“张老板,这价……?”
他吐出一口烟圈,眯着眼看伙计们忙活:“地骨皮这玩意儿,过了腊月二十,你就是出六十二也未必拿得到好货。药厂正月十五开工,仓库里得备足料。”他顿了顿,“做生意,有时候得看三步走一步。”
转到柴胡区,气氛却冷清得像另一个世界。药厂货六十五元,饮片货八十到九十元的价牌前,只有摊主老李独自守着炭火盆烤手。我蹲在他旁边的小马扎上,他往旁边挪了挪,让出点热气。
“今年这柴胡,”老李拨了拨炭火,“就跟这盆里的火似的,看着还有点儿亮,其实快凉透了。”
“不至于吧?六十五的价……”
“六十五?”老李苦笑,“去年这时候什么价?九十八!开春产地扩种了三成,库存堆得仓库都关不上门。”他拿起一根柴胡,指着上面的芦头,“你看,这么好的货,放往年得卖一百二。现在?八十都费劲。”
正说着,来了个老主顾。两人显然是熟识,连寒暄都省了。
“老李,六十,药厂货来五十公斤。”
“六十五,少一分不行。”
“六十二,现款。”
老李往炭盆里添了块炭,火星子噼啪响了几声。“六十四,这是底线了。你也知道,我从山西拉过来,光运费就……”
“六十三,不卖我走了。”
老李盯着炭火看了半晌,终于挥挥手:“装车吧。”
等主顾走了,老李才对我说:“瞧见没?这就是现在的行情。买卖双方都在试探底线,谁先撑不住,谁就亏。”他站起身,跺了跺冻麻的脚,“但话说回来,生意还得做。腊月里不把库存清一清,开春新货上来,更没戏。”
这时市场东头突然传来一阵喧哗。我跟着人群过去,看见枸杞摊前围了不少人。一个年轻人脸涨得通红,手里抓着一把枸杞:“你这280粒的货,分明掺了青海的!宁夏货我认得!”
摊主老周是个黑脸汉子,他不急不恼,从年轻人手里接过那把枸杞,又从自己摊上抓了一把,两把并排摆在白瓷盘里。“大伙儿都来看看,”他声音洪亮,“左边是这位小哥说我掺假的,右边是我摊上的。咱们用眼睛说话。”
人群凑近了看。老周接着说:“宁夏枸杞,果脐这儿有个白点,青海的没有。再看颜色,宁夏的暗红,青海的鲜红。最后你用手捏,宁夏的肉质厚实,青海的皮薄。”他把两把枸杞分别递给围观的老药商,“各位老师傅给掌掌眼。”
几个老药商轮流看了,纷纷点头:“左边这把,确实掺了青海的。”
年轻人愣住了:“可我……我就是在你这儿买的啊!”
老周从柜台底下摸出个账本,翻到某一页:“您昨天下午四点二十三,在我这儿买了三公斤宁夏枸杞,对不对?我这儿每笔生意都记账。”他把账本摊开,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时间、数量、单价。
“那这……”年轻人看着手里的枸杞,突然一拍脑袋,“我想起来了!我昨天还去了趟东区,是不是在那儿……”
人群里有人笑出声。老周摆摆手:“没事没事,弄清楚就好。枸杞这东西,最容易以次充好。您要是不嫌弃,今天再从我这儿拿点,给您按老顾客价。”
一场风波就这样化解了。人群散去时,我听见两个老药商低声议论:“老周这人实在,货真价不虚。”“要不怎么他家三代都在这市场做枸杞生意。”
已近晌午,我在肉苁蓉摊前碰到做饮片生意的老陈。他正拿着计算器按得噼啪响:“软大芸统货三十五到四十,中条四十五……老刘,你这价比上周贵了两块啊。”
摊主老刘是内蒙古人,说话带着草原的直爽:“陈哥,您也知道,今年雪大,产量本来就不行。这价,过了正月还得涨。”
“要是跌了呢?”老陈半开玩笑地问。
“跌了?”老刘哈哈大笑,“跌了您明年别来找我进货!”
两人相视一笑,老陈还是点了头:“那就来五十公斤,中条的。不过老刘,你得给我挑好的,别拿次货糊弄我。”
“瞧您说的,”老刘一边招呼伙计过磅,一边说,“咱们合作七年了,我糊弄过您一回吗?”
这笔生意就在这插科打诨中做成了。等老陈去交款时,老刘对我说:“做生意,说到底做的是人情。价钱可以谈,品质不能亏。一次亏了品质,十年攒下的人情就没了。”
今天中午了还是没有太阳,带着一些寒意,黄芩摊前突然热闹起来。价格涨到十六元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几个药厂采购几乎是跑着过来的。摊主是个年轻媳妇,手脚麻利地招呼着:“别急别急,都有都有!”
而一墙之隔的板蓝根摊却冷清得很。九到十元的价位已经维持了半个月,摊主老赵不急不躁,自顾自地泡着功夫茶。有熟人过来问价,他只笑笑:“开春再说,开春再说。”那份淡定,与隔壁的忙碌形成鲜明对比。
我转悠到市场最角落的艾叶摊。饮片货十二元,统货七到九元的价格牌前,站着一位老妇人。她看了很久,手指在口袋里摸索着,最后却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要走。
“阿婆,”摊主大姐叫住她,“您是要艾叶熏屋子吧?”
老妇人点点头:“儿子腰疼,想熏熏……算了,太贵了。”
大姐从摊上抓起一大把艾叶,用旧报纸包好:“您先拿去用,钱年后再给。”
“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大姐把纸包塞到老妇人手里,“腊月里,谁家没个难处。您先用着,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给。”
老妇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大姐转身看见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老人家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
“您不怕她不还钱?”
“怕什么?”大姐继续整理着摊位上的艾叶,“我做艾叶生意二十年,赊出去的账,十有八九都会还。真有不还的,那也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她顿了顿,“药材这东西,本来就是治病救人的。要是心里只想着钱,这生意做着也没意思。”
这番话让我在原地站了很久。在这个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的市场里,这份善意显得格外珍贵。
十二点钟,市场里的摊主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吃午饭。党参摊的老马一边盖苦布,一边对我念叨:“今年这行情……药厂货四十五,中条六十到六十五,比去年跌了三成。”他系好苦布的绳子,直起腰,“但你说怪不怪,越是这样,我越想好好做。等开春,我准备包片山地改种连翘——那东西,明年肯定行。”
“这么肯定?”
“肯定。”老马眼睛里有光,“药材市场跟种地一样,不能看今年什么价高就种什么。得看长远,看趋势。今年党参烂市,大家都改种别的,明年党参自然就少了。我现在守住品质,明年自然有人认我的货。”
这话说得通透。我帮他抬了一袋货,他非要塞给我两根党参:“拿回去炖汤,补气。”
当我终于走出市场时,外面的盒饭车前已经坐满了人,没什么生意的饭馆老板也走出店吆喝起来。身后传来摊主们互相闲聊的声音:
“老马,明儿还来吗?”
“来!还来四五天!”
“周老板,你那枸杞给我留两斤,我明天来拿!”
“好嘞!”
这些朴素的道别,在腊月的寒风里格外温暖。我忽然想起老周辨枸杞真伪时的认真,老刘做生意的爽快,艾叶大姐的善意,还有老马眼中的光。这个市场里,有人精于算计,有人坚守诚信;有人追逐涨跌,有人静待时机。而药材,就在这一买一卖、一进一出之间,完成了从泥土到药房的旅程。
腊月十六的这一天,地骨皮的跳涨,柴胡的冷清,枸杞摊前的风波,艾叶摊前的温情……这些看似平常的市井百态,其实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行情有涨跌,人心有冷暖,但日子总要一天天过,生意总要一单单做。守住本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