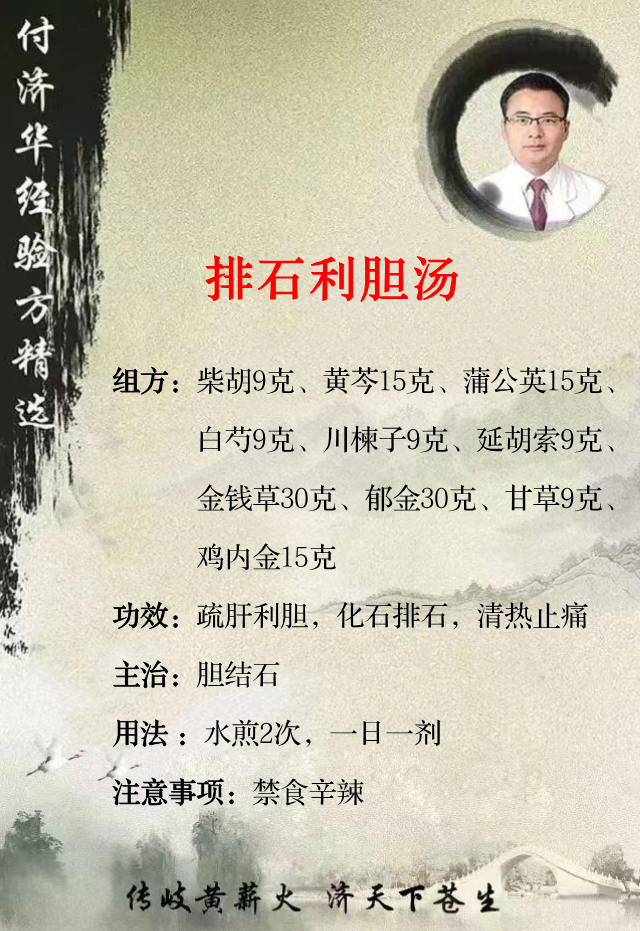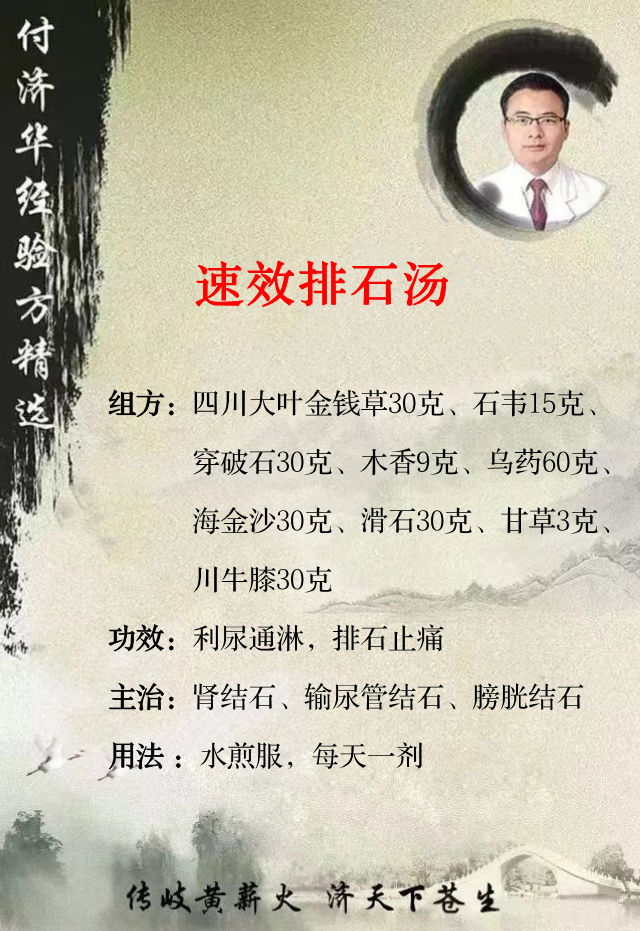早上刚刚六点半,药市门口的蒸糕摊已经支起来了,白茫茫的热气混着红糖的甜香,在清冷的空气里化开。
我挫着手走进市场,那股熟悉的、混杂着泥土、草根和陈木的味道便涌了过来,这是独活、苍术、艾叶,还有无数说不上名字的药材,在寒冬腊月里共同酝酿的气息。
独活摊子前果然聚了不少人。重庆巫溪产的货,价牌上“16”那个数字,用红粉笔描得又粗又重。摊主老马揣着袖子,脚边放了个小炭盆,不急不躁。“老马,你这心也太狠了,昨天不才十四块五?”说话的是个面生的四川客商,手里攥着一把独活片子,搓来搓去。
老马这才慢悠悠掏出手机,点开一段视频递过去。画面晃得厉害,是条盘山路,路面结着厚厚的冰壳,一辆货车歪在路边,半个轮子陷在雪里。“奉节那段,过不来了。就这一车货,您看着办。”那客商盯着屏幕,喉结动了动,半晌才说:“十五,我都要了。”
“十五块五。”老马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
两人僵持着。旁边看热闹的药农老张咳了一声,说了句公道话:“今年山里雪是大,路是真不好走。”这话像给了个台阶,四川客商松了口:“十五块三,现钱。”
“成。”老马这才露了笑脸,接过一沓钞票,沾着唾沫数起来。临了装袋,他抓起一把独活片,多塞进袋子里,“拿着,当个添头。”
转到苍术摊子,气氛就安静多了。山西来的野生货,半光的九十,刮得干净的光货一百零五。摊主徐爷戴着老花镜,正用把小刷子,仔仔细细刷着一块苍术疙瘩上的浮土。一个年轻后生蹲在旁边看,嘀咕道:“家种的才三十,差三倍多呢。”
徐爷头也不抬,把手里那块苍术递过去:“小伙子,你瞧瞧这个。”那后生接过来,对着光看。徐爷指着断面上一颗颗红棕色的小点:“这叫朱砂点。治风湿痹痛,靠的就是这点东西。家种的,长得肥,这个少。药效上,差出去可不止三倍。”后生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没说话,起身走了。徐爷也不留,继续刷他的苍术。
西边忽然一阵喧哗,是远志摊子。价牌上的数字被擦掉,又用粉笔重重写下“220”。河南来的采购老陈嗓门最大:“亳州报一百九!你这金子做的?”摊主是个利落的大姐,不跟他吵,从柜台底下摸出个硬壳账本,翻开一页指给他看:“瞧瞧,闻喜的货,抽芯率九成五往上。这成色,这年头您哪儿找去?”正说着,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快看!药通网说远志主产区下大雪了!”人群“嗡”地一下炸开,好几个人往前挤。大姐手快,抄起粉笔,在220后面又画了个向上的箭头,动作干脆得很。
市场深处,狗脊摊前冷冷清清。统片二十七。摊主老刘蹲在条凳上抽烟,一个老药农模样的顾客蹲在摊子前,拿起一块厚片,对着冬日微弱的阳光看纹路,嘴里喃喃:“好东西啊……祛风湿,强腰脚,现在坐办公室的年轻人,十个里八个用得着。”老刘吐了口烟圈:“是好东西,也是挖一棵少一棵的玩意儿。去年这时候二十五,明年?三十都未见得拿得到。”
最热闹的要数大枫子摊。价牌上“40”那个数字,写得张牙舞爪。摊主马大姐举着手机,屏幕冲着几个江浙口音的客商,嗓门亮得很:“……雨季!延长了!新货至少还得等仨月!就库房这点儿,卖完拉倒!”她直播间里人声嘈杂,似乎真有人在不停下单。“行!刘总五十公斤是吧?记下了!”她一边对着手机喊,一边麻利地扯过麻袋装货,嘴里还念念有词:“小东西,闹大动静,这市场啊,永远猜不透。”
艾叶摊子就在市场门口背风处,药厂货六块,纯叶子十一到十二。摊主是个眉眼和善的大姐,正低头把艾叶里的细梗一根根拣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围着旧头巾,在摊子前站了一会儿,看了看价牌,手在口袋里摸索半天,又缩了回去,转身慢慢要走。
“阿婆。”大姐叫住她,拿过一张黄草纸,手脚麻利地包了扎实的一包艾叶,递过去,“先拿去用。钱不急,年后再给一样的。”
老太太推辞,手有点抖。大姐直接把纸包塞进她提着的布兜里:“天冷,拿回去熏熏屋子,驱驱寒气。”老太太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眼眶有点红,转身走了。大姐继续低头拣她的艾叶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旁边的山药摊主老赵,捧着个搪瓷缸子,慢悠悠吹着热气。“六块五,毛条个子。”他对我笑笑,“这东西,老百姓家里的常客,价就得像它药性一样,得‘稳’。忽高忽低的,人心也慌。”
隔壁卖板蓝根的老李听见了,隔着摊子接话:“我那药厂货九块,统货十块,开春前也蹦跶不到哪儿去。急用的,自然会来寻。”
泽漆摊主老孙揣着袖子,乐呵呵地看着不远处为独活争得面红耳赤的人群,他的安徽统货就八、九块钱。“利水消肿的,是小众,”他眯着眼说,“可需要的人,离不了。价稳,心就稳。”
牡蛎摊前,个子两块,粒状的二块五。一个穿着洗得发白中山装的老先生,要了二十公斤个子货。摊主一边过秤一边搭话:“王大夫,又来进货了?”老先生点点头:“诊所里就指着这些平价药呢。价十年没大变,老百姓才用得起。”语气里有种历经风雨后的平淡。
中午,酸枣仁摊子前围了一圈人看热闹。国产98货四百五,95的四百四。摊主老周拿着块黑布,要蒙住一个年轻采购的眼睛。“别怕,尝尝。”他递过去两颗不同的枣仁。年轻人迟疑着放进嘴里,仔细咂摸:“这颗……先酸后回甘。这颗……没啥味,淡。”老周哈哈一笑,扯下黑布:“对喽!回甘的是河北邢台货,淡的是越南来的。怎么样,这学费交得值吧?”年轻人服了气,当场定了百十公斤。
日头刚好到正中央,市场的喧嚣渐渐沉淀。重楼摊子前,价牌上“62”的数字显得有点孤零零。摊主也姓马,正专心侍弄一盆文竹,剪掉枯黄的细叶。前年一百四的辉煌,像是上辈子的事。“都挤着种,可不就烂市了。”他剪下一段枯枝,“等这波人都熬不住,改种别的了,说不定机会又来了。”他顿了顿,眼睛看向远处,“开春,我也匀两亩地试试连翘。”
板蓝根的老李,望着自己空荡荡的摊位,点了根烟。“流感季过了嘛,”他吐出口烟,“价就得蹲着。等哪天又需要了,自然有人想起来。”
中午收摊的时候,艾叶摊前又来了位年轻母亲,牵着个咳嗽的小男孩。大姐包好艾叶,又顺手抓了一小把金黄的艾绒塞进去:“给孩子灸灸脚心,这个绒好,烟小,不呛。”这一幕,让隔壁正准备收摊的板蓝根老李看见了。他愣了下,转身从自己摊上拿了几包板蓝根,快步追上去,塞给那母亲:“配上这个,煮水喝,好得快些。”
那母亲连声道谢。老李摆摆手,走回来,对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咳,都是做药的,看不得孩子受罪。”
市场行人慢慢稀疏,摊主们陆续盖上一块块深蓝色的苦布。独活的狂热,远志的骚动,艾叶的温情,重楼的落寞,都被遮盖在下面。徐爷还没走,蹲在他摊子后面的小炭盆边,用铁棍慢慢拨着里面将熄未熄的余烬。
“看了半天,花红柳绿的,晕了吧?”他头也不回地问。
我想了想:“是有点。有人追涨杀跌,有人稳坐钓鱼台。”
“这就对了。”徐爷用铁棍夹起一块还有红心的炭,“市场就跟这火盆一样,有烧得旺的时候,有看着要灭的时候。”他把那块炭轻轻放在灰堆上面,吹了一口气,几点火星子飘起来,炭块隐隐又有了红光。“可只要芯子里还有一点热乎气,给点风,它就能再着起来。”
他站起身,捶了捶腰:“药啊,跟人一样,贵在守得住自己的‘性’。独活就该祛风除湿,艾叶就该温经止血,板蓝根就该清热解毒。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了,外头价高价低,刮风下雨,心里头那杆秤,它就不会歪。”
我走出市场,冷风一吹,头脑清醒了许多。回头望去,市场里还有着三三两两的行人提着打包小包,商户有的拿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午餐开始吃着,有的走向街边的盒饭摊。那些算计、争执、温情和坚守,都暂时按下暂停键。但我知道,等那盖上的苦布再揭开,一切又会活过来,带着草药特有的苦涩与芬芳,继续讲述着关于生存、关于得失,也关于一丝未泯的温热良心的故事。
记得下面的点赞👍、分享、小心心❤️,有问题下面留言,我们都会一一回复的!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