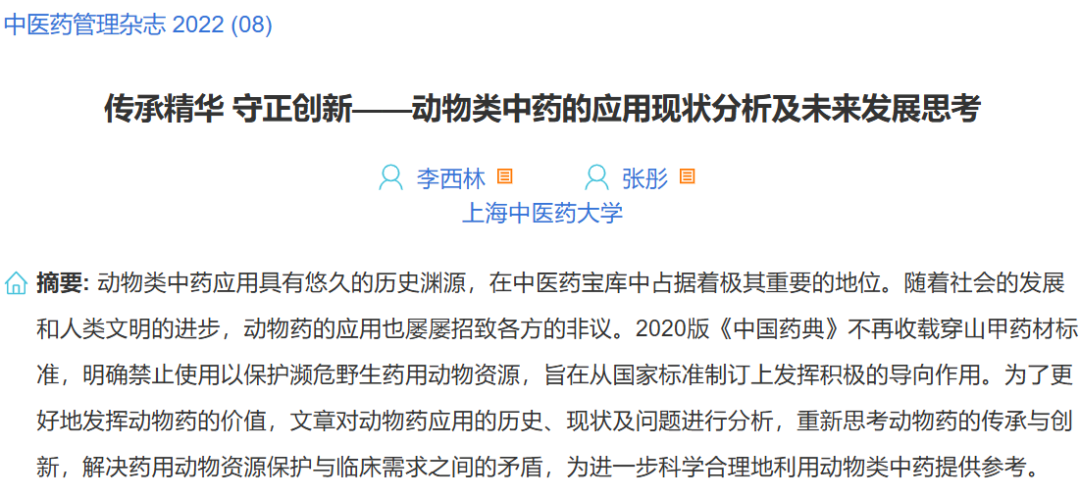
动物药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活性强、疗效佳、显效快、潜力大、应用广”等特点。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味药材,其中动物药65味,占17.8%。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共收载动物药51种,较2015年版减少了穿山甲。中医临床常用的药材约300种,其中动物药占10%左右。常用的动物药尽管数量不多,但在配方中使用的频率却很高,约有1/3的配方中会出现。动物药具有清热泻火、散风解毒、祛风湿、平肝息风、活血祛瘀、补益生津、攻毒等功效。除药用外,在食疗方面,动物药的需求更大,由于药食两用价值突出,因此需求量不断增加。由于药用动物多来自天然,其中不少为濒危动物。由此野生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动物药紧缺、质量下降和伪劣药材充斥市场,而且还是不少优质中成药停产退市的直接或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位动物药,对其进行科学实验及客观评价。在临床应用时,要从病情实际需要出发,合理用药,做到既传承发展中医药,又保护珍贵的动物资源,实现动物药的可持续利用。
1 中医学对动物药应用的朴素观念
动物药在我国应用历史悠久,中医学认为,动物药属“血肉有情之品”。《五十二病方》记载了73种动物药,包括兽类、虫类、人类、禽类和鱼类等,占药物总数的26.53%。清代医家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指出:“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写道:“降人一等,禽与兽也;降禽兽一等,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与石也;用药治病者,用偏以矫其偏。”
从历代本草文献看,有关动物药功效的记载,大多以该动物的生活习性、体态特征为隐喻认知来源。通过对动物习性、体态的观察,以及取象比类的假设,对动物药的功效进行解释。以动物的组织或器官入药,其功效多取自于其“形”“质”等特征,这体现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如中医的“以脏补脏”“同气相求”就属于朴素的“取象比类”“天人合一”理论,由此形成了以骨补骨、以肉生肌、以血补血、以髓补髓等理念,用以补益人体相应组织器官的虚弱。基于“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虎为“百兽之王”,虎虎生威由此成为民间的大补药,虎骨具有壮筋骨、祛风湿的功效。牛黄为牛的胆囊、肝胆管结石。李时珍云“牛有病在心肝胆之间,还以治人之心肝胆之痛”,表明牛黄具有息风止痉、化痰开窍、清热解毒的功效。李时珍还云:“鹿乃仙兽,纯阳多寿,能通督脉,又食良草,故其角肉食之有益。”由此鹿茸具有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的功效。鹿具有鹿首回头向尾的生存习性,由此判断鹿能通督脉[1][2]。
鳖白天在岸边晒背甲,夜晚潜入水底,根据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滋阴潜阳、阴阳调节在鳖的生存习性中得以充分体现,故以鳖甲入药,取其滋阴潜阳的功效。李时珍云:“龟鹿皆灵而寿,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其甲以补心、补肾、补血,以养阴也。”用龟甲取其滋阴潜阳、益肾健骨、退虚热的功效。吴仪洛云:“蛇善行数蜕,如风之善行数变,故能内走脏腑,外彻皮肤,透骨搜风,截惊定搐,治风湿瘫痪。”蛇具有抗风湿习性,否则无法生存。这一特性为人所用,如金钱白花蛇、乌梢蛇、蕲蛇等蛇类药材具有祛风湿的功效[3]。地龙、全蝎、蜈蚣等虫类药属“行走通窜之物”,大多具有活血化瘀、搜风通络功效。张仲景首创虫类搜剔通络法,创制了以虫类药为主的抵当丸、大黄 虫丸等方剂[4]。近代孟河医派章次公尤善用僵蚕、蝎尾治中风,地龙治咳喘,九香虫治疗胃脘痛等[5]。
虫丸等方剂[4]。近代孟河医派章次公尤善用僵蚕、蝎尾治中风,地龙治咳喘,九香虫治疗胃脘痛等[5]。
2 认识水平的局限对“食补”的盲目推崇
出于好奇和猎奇心理,以及对“食补”的盲目推崇和迷信,很多不应该被端上餐桌的动物被大量捕杀,而出现在餐桌上。从古至今,“药食同源”理论备受历代不少医家推崇,他们采用动物药辅助疾病治疗,以达到“食补”的效果。有相当数量的动物被供食用,因而导致动物药愈发昂贵和稀缺。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用于配合治疗的饮食调养配方就有不少动物药,如著名的当归生姜羊肉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等。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也使用了大量动物药作为食疗方,如妇人养胎中的乌雌鸡汤、雉鸡汤。张从正的天真丸以紫河车为君药,辅以地黄、当归、白术、砂仁等药,用于调和气血,治疗虚损。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以猪脊髓、龟甲滋阴补髓,又以羊肉、龟甲、虎胫骨制成虎潜丸,治疗精血不足之“脚痿”[6]。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记录了阿胶、鹿角胶、鹿茸、紫河车、龟甲、人乳粉、牛羊猪脊髓等多种动物作为补益药治疗虚劳诸症,以调和气血,滋补强壮机体[7]。
对于动物药的功效,有的尚难以证明其有效性,对这些动物药应少用甚至不用。对一些沿用的动物药要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和实验研究,通过成分分析和药理作用研究等,证实其使用价值和治疗效果,坚决淘汰那似是而非、疗效不明显的动物药,不迷信,不夸大其功效,消除猎奇攀比现象,从病情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药物,避免因养生保健和临床治病心切,或盲目认为珍稀动物的“大补”功效而滥用。孙思邈在使用动物药治病救人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自古明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这充分体现了古代医家尊重生命的崇高思想和道德情操。
3 药用动物资源保护的迫切性
药用动物多来自天然资源,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大。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动物栖息地的减少、滥捕滥杀现象严重,药用动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权威信息发布,全球超过1.7万物种入围其2009年“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可能有灭绝危险。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162种药用动物中,林麝、黑熊、马鹿、中国林蛙、蛤蚧等40个种类的资源显著减少。参照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协议,虎骨、犀角等濒危物种已被明令禁止作为动物药使用。《实用中成药物手册》列出了158种中成药含有濒危或受保护的药用野生动物,涉及15个种类的保护动物,如犀角、虎骨、麝香、牛黄、羚羊角等。由于需求量增加,乱捕乱杀导致药用动物衰退甚至濒临灭绝。
4 动物类药材的应用现状及问题
4.1 动物药的应用
据统计,约有30%的中药配方会用到动物药,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传统中成药,如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六神丸、麝香保心丸、片仔癀、西黄丸、牛黄清心丸等。动物类药材,如麝香、牛黄、熊胆、羚羊角等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可或缺且无法取代。“缺了动物药,名方将不复存在”已成为业界的担忧。与此同时,动物药的使用不可避免地会直接影响甚至剥夺动物们的生存权利。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尊重生命,保护动物的呼声越来越高,药用动物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动物药的应用面临重重困境,动物类药材的使用遭到国内外多方的质疑和非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4.2 动物药所存在的质量问题
相对于植物类中药材,动物类中药材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可能存在的质量安全风险点更多,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影响动物药品质的因素较多,如遗传、环境、养殖、加工、炮制、储藏、包装、运输等。动物药往往一药多源,来自不同基源种的动物往往会作为同一味中药使用,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等现象长期存在。部分动物类药材在采集、炮制、加工、贮藏及使用等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由于养殖加工、生产贮存过程不规范,动物药抗生素残留超标,更容易变质腐烂,也是黄曲霉菌素的高危感染品种;功能主治广泛,但其药效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却不明确,稳定性差,容易变性,检验缺乏对照品,检测手段复杂,成本高,缺乏专属性鉴别方法和质量控制指标,重现性差,难以建立有效地测定成分及质量标准。药源紧缺是导致药材质量下降和生产伪劣药材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随着环境的变化,药用动物资源逐渐减少,市场供不应求,除导致动物药的价格不断上涨外,还出现了大量伪品、劣品、混淆品、习用品,严重影响了药材及其制剂的质量。目前动物类中药材普遍存在质量标准不完善的问题,加之药材在运输、保存过程中受污染、变质,影响了治疗效果。因为不能保证其质量的均一性,所以难以保证其生物有效性和用药安全性[7]。2020版《中国药典》对于动物药的质量控制标准有了较大提升,一部收载51种动物药均有性状鉴别,其中18种动物药收载了显微鉴别,25种动物药收载了化学鉴别,3种爬行类动物药收载了聚合酶链式反应法,22种动物药收载了含量测定[8][9]。
4.3 动物药的弊端分析
动物药本身有其不足与短板,它可能带来致病性、过敏性和胃肠道不适应性。不少野生动物身上带着人类未知的病毒和寄生虫,异性蛋白可能产生的过敏反应,这些对于使用者来说都存在极大的风险,有的甚至是致命的。有的动物药具有较重的恶臭气味,对胃肠道黏膜的刺激性很大,服药的依从性较差,有些胃肠虚弱的人服后可能会出现腹胀、恶心、泛酸和呕吐等胃肠道不适反应,这既不利于患者服药,也不利于药物有效成分的吸收,甚至会适得其反[10]。
5 动物药应用与资源保护建议
5.1 开展野生动物资源普查,人工饲养繁殖逐步替代野外捕杀
建立“中国濒危药用动物数据库和物种资源库”及“中国濒危药用动物标本中心”,加大生物资源保护的国际公约及我国生物资源保护法律、法规、法令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对乱捕滥杀动物和破坏其生存环境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加快建立自然保护区,确保药用动物资源的恢复,提高蕴藏量。解决资源的匮乏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开展对野生动物的人工繁殖,这是合理利用药用动物资源的发展方向。对尚未被禁用的麝香、牛黄、熊胆、羚羊角等名贵药材,采用人工繁养的动物代替猎杀野生动物,加强人工驯化、繁殖的研究与推广,变野生为家养。目前已成功建立了鹿、麝、熊、哈士蟆、全蝎、蜈蚣、龟鳖及蛇类等人工驯养繁殖场,旨在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动物药的驯化养殖是保障动物药供给的主要途径,可以有效解决野生资源枯竭和养殖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中医临床无药可用的难题[11]。
5.2 加强动物药物质基础及替代品研究
中药的功效与其“形”“质”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但这并不与现代中药所指的药效活性成分具有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动物药的药效组分研究,确定其发挥药效作用的物质基础。建立生物类群、化学成分与药效活性之间相互联系,与化学、药理研究工作紧密配合,在一定的动物类群中寻找活性强的化学物质或扩大新药源。在天然动物药材紧缺的情况下,采用人工制品、人工合成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充方法,有助于缓解临床对常用名贵天然药用动物资源的长期过度依赖。目前市场上研制成功的替代品,如人工牛黄、人工麝香、人工熊胆等对于保护这些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开展珍稀濒危动物药的替代品研究开发已成为中医药界共同关注和科技攻关的重要课题[12]。
5.3 通过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建立动物药工厂
开展濒危药用动物细胞工程研究,利用组织细胞培养、中间代谢产物或培养液,从中诱生或分离具有生理活性的物质,进而达到保护濒危药用动物的目的。对于濒危药用动物的优良生产性基因,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转基因动物,定向生产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和改造天然活性成分,使转基因的动物成为中药活性成分的活体工厂即“动物药品工厂”,使濒危药用动物资源从传统的自然获得逐步转向走产业化生产道路。对缓解动物药的紧缺、保证临床用药和制药需求、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5.4 新技术应用于动物药的质量控制
目前,动物药功效的物质基础、质量评价研究等尚不够系统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动物药的临床使用和制药工艺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应用与发展。准确鉴定动物药材的基原物种是确保其临床使用安全有效的前提。动物药经过干燥炮制加工后面目全非,采用传统的性状和显微鉴定方法往往无能为力。DNA条形码作为一种新兴的分子鉴定技术,是对常规鉴定方法的有效补充。中国中医科学院提出了动物类中药材分子鉴定的研究策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动物类中药材的DNA提取方法,并建立了动物类中药材DNA条形码数据库。陈振江[13]等用SDS-PAGE获得人工牛黄、鹿蹄筋、蝮蛇、乌梢蛇、金钱白花蛇及其伪品的清晰电泳谱带,为蛇类药材、人工牛黄、鹿蹄筋及其制剂的生产、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刘中权[14]等建立了简便、实用的龟甲药材DNA分子鉴定方法,所设计的鉴别引物对乌龟有高度特异性,与性状鉴定和DNA序列分析鉴定结果完全一致。许亚春[15]等应用DNA条形码技术对熊胆粉及混伪品进行鉴定研究,以保证熊胆粉的安全有效利用。刘睿[16]等基于“蛋白质/肽组学-修饰组学”研究动物药蛋白质、肽类物质与功效关联规律的思路及方法,对角类、胶类动物药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传统功效、成分和修饰组间的规律性与关联性,为中药动物药现代化研究和功效物质基础研究等提供了借鉴。宫瑞泽[17]等采用中药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 Q-Marker)方法构建鹿茸质量评价标准体系,解决了基原复杂、品种混乱等问题,推动了鹿茸质量控制标准提升和规范鹿业市场,对于保证动物类中药材质量和控制生物安全隐患提供了研究思路。
6 结语
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更是所有生物的家园,濒危药用动物保护再生体系与药用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始终处于对立和矛盾之中。中医药不是造成野生动植物濒危的“元凶”,但也不能成为“帮凶”。我国已全面禁止犀角、虎骨和濒危动物的药用,限制使用天然麝香、天然牛黄等一些珍稀动植物中药资源使用范围。自2010版《中国药典》后不再新增收载濒危野生动物药材,而是引导用体外牛黄、人工麝香、人工虎骨等替代品用于药材。穿山甲已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Ⅰ名录,2020版《中国药典》不再收载穿山甲药材标准,对于动物药的应用所采取的理性而果断措施,旨在从国家标准上积极引导动物药应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这些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内容,应该融入中医药类专业核心课程设计中,在课程思政中予以充分体现,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以保证动物药在维护人类健康中的合理使用,推进中药现代化走上可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道路。
